周重林:岌岌可危的中国茶 2023-01-30 18:30:48 作者:周重林 来源:浦睿文化 浏览:

以下文章来源于浦睿文化,作者周重林
中国内地因为外商资本的入侵,茶叶进入全球贸易竞争之中,各产茶区的情况很不好。李文治编的《中国近代农业史料》和姚贤镐编的《中国近代贸易资料》与彭泽益编的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》里,都网络了许多晚清茶业有关的文献资料。阅读这些文字以及背后传达出的焦灼,让人难安,一个茶叶大国,怎么会走到这般地步?
湖南胡林翼上报说,“承示茶贩多系大商,现又多领洋人本钱,加之未尝不可,即舍湖南过境之茶厘,而加本省出产之茶厘,所得尤多一节,应请尊处核稿代印示行为要。”这是针对茶税而言,每过一地要收费一次,让成本增加。
晚清茶税政策与其他进口产品比起来,非常不合理,出口是重税,但进口却收费很低。在一家垄断贸易的情况下可以理解,但现在三家竞争国际市场,咸丰年间茶税不但不降,反而收得更高。日本人、英国人为了促进茶叶销售,基本都是免收出口茶叶税。
湖南的情况与安徽的情况差不多,曾国荃在《请免加茶课疏》里说,以前茶叶走甘肃内销,是我们说了算,茶商可以操控价格,但现在安徽茶都销售给外国人,且仅限于上海一地,往往都是借外商的钱,再去收茶,无奈今年茶叶价格骤跌,贷款期限又到,茶商只有折本茶叶,为了减小损失,只能求减免茶税。
1884年汉口海关贸易报告称,经营茶叶的华商经常是靠贷款经营,他们向生产者卖茶,之后转售洋商。今年可供借贷的款子不多,并且利息高,借款期限短。结果,当茶市快要过去之时,贷款就要到期。华商就这样,在外商的压迫下,被迫卖茶偿债。
1887年的海关报告说,仅茶一项中国一个季度的损失不下100万两白银,针对中国茶叶颓势,赫德受到总理衙门的委派后,研究对策。1887年总税务司印行了“访查茶叶情形文件”。
普遍认为,中茶难销,主要问题还是印茶价低,因用机器以揉茶叶,或检或焙,皆用机器,不费人工,用火车搬运,载费亦省。后面的分析更令人难安:“1876年,印茶每磅1先令5便士,1886年则仅值9便士5,相差约有一半,估计再过2年,印度每磅茶价还会下降,到6便士”,“诚如是,则寰宇以内辨茶之人,嗣后恐不必拘于中国、印度,势将争趋于茶价最贱之区贩运矣。况近来印度茶在英每年多销售中国茶有700磅,已见端倪。”
从中英两国的茶叶发展看来,由英国人掌控的中国各地海关的茶叶调查报告,其实不仅仅是为了中国人,更是为英国人如何打开市场做准备。我们看看由英国在各海关上报的调查。
中国茶面临的不仅仅是印度茶,还有日本茶的竞争。美国人是中国绿茶的大户,但这个市场被瓜分得较多。令人奇怪的是,他们并没有分析真正的购中国茶大户俄罗斯,英国人重点分析美国,难道是想把印度茶打入美国市场?
日本人的茶,不仅与中国再比出口美国的数量,还返销到了中国。这些茶是从天津入关,主销华北地区。因为价格便宜,从日本过来也有赚头,而销售的商人也以“华茶”称之。这与英国人开始在英国推销印度茶谎称是“华茶”的手法如同一辙。还有一个例子也能说明问题,因为太平天国占领了东南的主要茶区,这带茶很难弄到,但习惯喝福建茶的俄国人又非要福建茶,茶商只要用湖北、湖南茶当作福建茶卖,没有想到这些茶更适合俄国人的口味,后来运去的真福建茶,他们还不要了。所以,喝茶讲口感这种事情,对非产茶地而言,几乎是商人说了算。
查茶叶不但本产于中国,且中国茶叶之味较他处尤佳。而中国茶叶虽出口者年比年增,有多无少,然英国所需茶之人,较前倍多,其倍多之人,大半不需中国之红茶,而购印度之茶。即美国近日需茶情形亦然,其倍多之人大半不需中国之绿茶,而购日本之茶。推原其故,并非中国茶料之逊,实以印度日本之茶,备办出口者,俱加意留心,一无亏假,直至需茶者之手,始终不变。且其价值,亦较中国为廉。(访察茶叶情形文件,页4,总税务司申呈总理衙门,光绪十四年七月二十四日)
印茶和日本茶,仅仅是因为价格低廉,就受到欢迎吗?如果是这样,那么可以通过减税、降低价格来解决问题,但更深层次的原因,就一时难以解决。综合当时国内国外的材料分析,主要原因还是通五口通商以来,各地衙门和茶农纷纷把茶叶作为创造利润主打产品来做,在福建一些地方,还有人用良田来种植茶叶,在中国茶一家独大甚至垄断的情况下,这无可厚非,有那么多想赚钱的国内外商人,他们会把这独一无二的商品很卖力地推到世界每个角落去。
但随着大量资本进入到茶行业,扩建茶园(茶叶种植面积每年都在扩大)、制茶中心(各种茶叶粗制所设立)、转运中心(因茶而兴起了许多城镇)都成规模的情况下,却忽然杀出像日本、印度这样来势汹汹的对手,许多人估计连第一个“五年计划”都没有实现,就赶上了全球茶叶供求过剩——茶叶由卖方进入到买方市场的困境,不乱套不惊恐才怪?
而且,出问题的主要是面向外贸的茶叶,传统的中国大茶商,主要是走内销和边销茶,他们并没有受到太多冲击。老外有一份报告就注意到,与其一味追求出口,还不如回到内销,中国本身就是茶叶消费大国,这点是日本和印度也无法比拟的。当然,这种论调今天还在国内很流行,确实也是如此,中国最好的茶叶,一直以来连内销都供应不上,根本不用琢磨着怎么去卖到国外。
赫德最后分析认为中茶与印茶相比,失去竞争力的原因有三个:一、英国人善于将各处之茶合归公司统领。二、用机器配置,这可以提高效率。三、讲求经验良法,装焙茶叶,以期省费价廉。印度公司茶园产量很高,每亩33斤至87斤不等。汉口海关的报告,除了赫德所说的资本、机器、制法外,还提到了廉价的劳动力、化学和农业知识、消费者偏好和需求、便利的交通、就近消费地、灌溉工程、大茶园等。
中国后来也学了,结果呢?大量使用化肥后,带来了农残超标,又只好回到传统的老路上,换个新名词——有机茶。劳动力,中国自然比不上印度那么多廉价劳工,但是中国进口过来的机器有几台能用上?杨克成在回忆大理“永昌祥”做茶的时候说,他们进口了三台机器,三年都没有组装,因为完全没有必要,茶忙的时候有上千妇女在帮忙,那些机器根本用不上。
茶叶是一个季节性的物品,并非需要全年都在茶山上忙碌。
所谓消费偏好就是我们不喝红茶,但英国人喜欢,那就要多生产红茶。这里需要说明下,历史上许多喝茶法是源于一场误会,中国的概念里,绿茶才是茶。
我们今天所熟知的茶叶分类,不管是叫绿茶、红茶还是青茶、黄茶、白茶、黑茶,或者称为发酵茶、半发酵茶、不发酵茶、后发酵茶,所谓六大类、四大酵都是为了与绿茶做出区别,这一切都是建立对绿茶的认识基础之上。
鼓吹中国茶史有几千年,可是在明代以前,我们所看到、听到的茶都是绿茶。在唐代,倘若一个人在花下喝茶,会被当作一件极为煞风景的俗事,要被那些文人士大夫笑掉大牙;可是到了明代,在茶里加点花花草草变得很流行,花茶就是这么发展起来的。
明代是一个物质社会高度发展的年代,除了花茶(还是绿茶的一种花样喝法而已),黄茶、黑茶、白茶、青茶也陆续被那些手艺很歪的工匠不小心研制出来,他们在制作绿茶的过程中,总是采用不正当不及时的加工方法,顶着不善制法的恶名被炒鱿鱼,也许要过很多年来能缓过神经来正视自己的伟大创造。
冒犯绿茶,就是冒犯传统。
黄茶的制造者被许次纾在《茶疏》里贬得一探糊涂,他斩钉截铁地说,这帮庸才作废了的绿茶,是下等人的食物,算不上饮品。现在很难遇到喝黄茶的人了,就连湖南、安徽这些黄茶主产地,也很少看到有人喝黄茶,他们最终还是选择了绿茶这个传统。我偶然间喝过君山银针、蒙山黄芽,觉得很不错,但真的很难推广开。
嘉靖年间的御史陈讲疏说,四川、湖南的黑茶,只是销边换马的物资,算不上什么好茶,最多也是中二品而已。黑茶当时不过是废品黄茶的替代品,黑取代黄,动摇不了绿,黑黄都是主流消费群弃用之后,打发给那些想喝茶又没银子的人打打牙祭。当时有一种骇人的观点说,黑黄茶都是用来漱口洗脚养花的,只有绿茶才是用来品饮的。
红茶是日晒代替炒青后出现的,首先现身在福建崇安的小作坊里,满足一些民间茶爱好者换嘴瘾的需求。安徽人余干臣从福建罢官回安徽老家,把红茶的制作工艺带回了祁门,研发出了对后世影响巨大的祁门红茶。但习惯了绿茶口味的国人对红茶始终热爱不起来,一阵流行风过后,他们还是各自端起了绿茶杯。
就是喝茶时间和部位,也发展得非常不一样。唐代没有听过谁喝茶芽,当时是煮茶叶喝,基本上老叶子再加点盐巴之类的才有滋味。宋代喝茶末,大家斗茶玩,一个茶饼摆好几年,陈茶谁都不介意,工具主要是盏碗,日本人就是学的宋代喝法。明清之季,喝新茶之风从江南一带传开,工具也换成了紫砂壶与瓷器,有人发现茶芽不错呀,看着也舒服,清饮遂流行至今。
绿茶容易变质、发霉,明代、清代几乎每隔几年都在西北的茶马司(或其他茶叶机构)大甩卖清仓,许多老百姓多年下来,喝陈茶早就习惯了。你给他喝新茶,他还说你蒙他。英国人长途跋涉运回去的绿茶,会有多好喝?
在苏伊士运河没有开通前,他们最快也要半年,终日在大海上,更会加速绿茶的变化,比较来说,全发酵的红茶受到的影响就要小得多。商人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口味,恰好又赶上白糖在英国的同时崛起,说真的,要是离开了白糖,大英帝国不会那么快形成全民饮茶的风尚。
也有不少人认为,当年英国人正是为了喝点新鲜茶叶,才发明了快艇技术,进而不惜代价拿下埃及,打通苏伊士运河。
许多研究经济贸易的人,对茶完全不了解,只看看数据,老外说了什么,算算成本和利润,就痛心疾首地喊,你们怎么不像印度学习之类。中国茶业之所以从衰退到后面全面退出,造成今日“一个国家茶叶销量赶不上一家英国公司”之困局,就在于向印度学坏了,或者学歪了。不是任何一样都是别人好,更何况这是我们引以为豪的“国饮”。
1898年,中国近代农学的开创人、古文字专家罗振玉为皖南茶厘总局道台程雨亭的《整饬皖茶文牍》作序时,言及中国茶、丝,显得忧心忡忡,“顾近年以来,印锡产茶日旺,中茶滞销;日本蚕丝又骎骎驾中国而上,利源日涸,忧世者慨焉。”明以来,茶、丝是中国向世界输出的最大宗物品,但到晚清,中国的老大地位受到严重挑战,担忧论调成为茶、丝主题最为显著的基调。
程雨亭在《整饬皖茶文牍》的系列文告中,直言中国茶叶的地位岌岌可危。一方面,分散的小民经济,受不了茶叶市场供需关系的屡变,尤其是在茶叶十分之九都依赖外贸的情况下,又受制于外商公司的大资本;另一方面,为了追逐短暂利益,许多中国茶商造假之风盛烈,茶商们为了赶时间,居然用柴炭熏焙,而不用锅焙炒。
所谓“绿茶染色,红茶馋土”更有甚者,制造出了一种叫“绿茶阴光”假茶,里面搀和滑石粉,颜色倒是出彩,但饮用者出现了腹疼情况。可叹的是,在歙县30余号茶庄中,不做这种茶的寥寥可数。
在绿茶中加“滑石粉”,被胡秉枢写进了向日本人推广茶叶的《茶务佥载》中,对西方人不喜滑石粉颇有微词,认为在绿茶粉中加这点料是必须的一个程序。这就是说,至少在当时的中国茶人看来,这并非造假,而是更高级的茶叶形态。
(节选自《茶叶战争:茶运与国运》,周重林,太俊林著,蒲睿/湖南人民出版社)
作者简介:周重林,学者,作家,著有《茶之基本》《茶叶战争》等多部畅销茶书。
图文转自茶业复兴,经“茶业复兴”授权爱普茶网转载,观点仅代表作者个人。
上一篇:2023年2月2日晚上八点,昌金强《云南沱茶·销法沱》品读会
下一篇:最后一页


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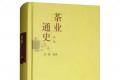


 备案号:
备案号: